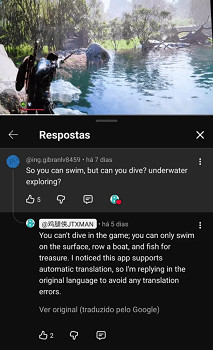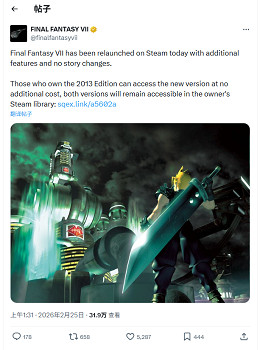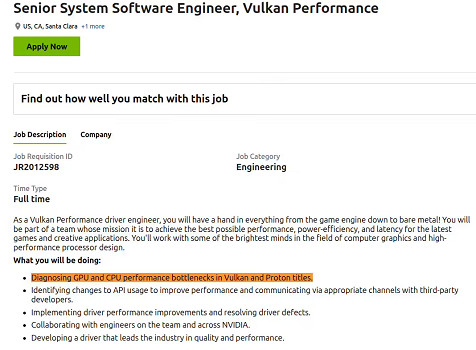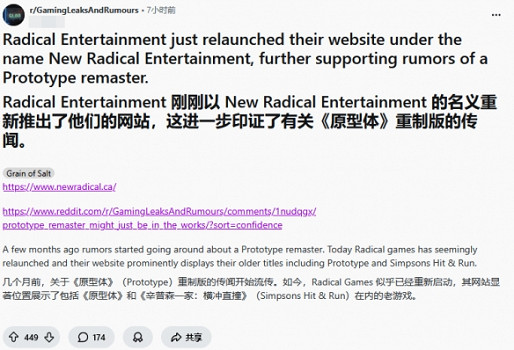一篇源自Kotaku的報導詳細介紹了開發時間漫長、成本巨大且過程坎坷的育碧新加坡遊戲《怒海戰記》的創作歷程。原文作者為Kotaku編輯Ethan Gach,翻譯為陌離@其樂Keylol完成。
《怒海戰記》的漫長開發歷程:育碧新加坡的8年噩夢

有些人說這個項目真是活見鬼。還有些人單純只是不知道他們該做出一個什麽樣的遊戲, “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幹什麽。” 一名前開發者說道。
《怒海戰記》的開發早在2013年就已經開始。據三名知悉項目內情的消息源透露,起初這個遊戲打算以《刺客教條4:黑旗》多人資料片的形式進行後續更新。不過,這個 “資料片” 越做越大,一個完整的大型多人線上遊戲初具雛形。於是,它便獨立出來,以《黑旗無限》的名號繼續開發。再後來,它被賦予了全新的名字,這就是《怒海戰記》。
在2017年的E3遊戲展上,《怒海戰記》憑借著播片和實際上手試玩引發了大量關注。次年,它又帶來了另一個經過仔細打磨的試玩。但在此之後,有關這個遊戲的消息便石沉大海。其間發生了什麽,消息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表示,儘管在E3上大受好評,但這個遊戲在當時壓根就不存在;另外一些人卻說,當時在展會上提供試玩的版本已經可以大致趕上搶先體驗,等待發布之後再不斷完善,就像其他長期更新的線上多人遊戲(也稱 “遊戲即服務” ,games-as-a-service, GaaS)做的一樣。
這麽多年來,這個遊戲依然沒有像模像樣的成品,參與其中的開發者們的努力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許多工作沒有任何意義,” 一名前開發者表示, “在這個基礎上打磨作品僅僅只是浪費時間。”
《怒海戰記》原定2018年末發布,後來變成了2019年內,不久這個日期變成了2020年3月之後,然後又是2022年3月之前。至於現在,它預計將於2023年3月之前發售。
在短短三年內宣布四次大延期,這個成績哪怕是出自對 “跳票” 習以為常的育碧,也不得不讓人對這個項目及其開發者的前途和命運捏把汗。《怒海戰記》也許終有一天會發售,成品可能還相當不錯。不過從現在來看,他們在開發這個遊戲的過程中,幾乎把一個大廠能踩的坑都踩了個遍。
“沒人相信明年2月能發售,但你總會期待。” 在育碧五月的財報會議宣布遊戲將再度延期之後,一名現任員工告訴Kotaku。
在財報會議上,育碧高層們艱難解釋著又一次延期背後的原因。
“在新加坡工作室的主導下,遊戲的製作在過去一年內正穩步推進,其前景也值得期待。” 弗雷德裡克·迪蓋(Frederick Duguet),育碧的首席財務官在會議上說, “選擇延期能讓團隊充分實現他們對遊戲的設想。”
但是,在採訪了超過20名現任或前任育碧工作室的開發者、對遊戲開發過程知情的相關人士、其他參與開發的員工之後,事情呈現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們接受採訪稱,《怒海戰記》團隊對於遊戲從未有過明確的設想。整個項目苦於經理們彼此間的權力爭鬥,以及每年都要經歷一次的項目重啟和時不時的小修小補。開發歷時如此之久,然而有關遊戲核心設計的一些最基礎問題依然沒有定下來,哪怕像是遊戲是否要採取長期更新形式的提案,也在高層的辦公桌上越堆越多,無人過問。
所有受訪者都準予匿名,因為他們並未獲得向媒體披露項目有關訊息的許可,或擔心公開議論前雇主的是非會給自己在遊戲領域的職業生涯蒙上汙點。
自立項已經過去了八年,可想而知的是《怒海戰記》早已花光了最開始的預算。根據三個消息源,這個項目從育碧那裡獲得了超過1.2億美 (約新台幣33億多元) 的支援。而且,為了盡快讓遊戲發售,來自其他工作室的上百名開發者源源不斷地被調撥來填補漏洞。預算數字隻增不減。
根據他們參與過的遊戲項目的銷量,育碧員工可以獲得相應的獎金激勵。有些員工長期參與 “年貨” 遊戲,例如《刺客教條》系列的開發,因此他們每年都能保證得到可觀的收入。不過,根據消息源的說法,《怒海戰記》項目深陷泥潭,整個團隊只能為員工的薪水做銷記,以保證他們還有機會發出獎金。
“沒人願意承認他們搞砸了。” 一名員工表示, “這個項目和那些美國銀行一樣;它們規模太大,承擔不起失敗的風險。”
“像《怒海戰記》這個項目的情況,要是在其他廠商那裡,它早就被斃掉至少十次了。” 一名前員工說。

另一名前員工說,有些廠商比如EA或者T2甚至都不會給這種遊戲立項。不管怎樣,育碧為這款多人海盜冒險遊戲下了大注,無論如何也鐵了心要讓它發售。也有部分原因是,這類的服務型遊戲愈發成為育碧財務報表上盈利的頂梁柱。不過,也有三個消息源告訴Kotaku,新加坡政府也要求這個遊戲必須發售。他們表示,為了獲得新加坡政府的補貼,育碧在新加坡的工作室不僅要雇傭一定數量的員工,還要在數年內推出由新加坡工作室原創的IP。
遊戲開發拖延了數年,但許多現任和前任開發者都表示,他們還沒有太多拿得出手的東西。一名現員工把《怒海戰記》坎坷的開發歷程與生軟(Bioware)的《冒險聖歌》比了比:《冒險聖歌》也是一款計劃長期更新的大型多人遊戲,它的實機展示看上去很不錯,但發售的成品尚未完善,遊戲內容也支離破碎。《怒海戰記》核心團隊裡的成員認為,他們依然有希望不走《冒險聖歌》的老路;可是,他們同樣覺得把遊戲做完、開啟新項目的目標難以實現。
“四五年都做同一件事情卻一點進展都沒有,這真的很打擊人。” 一名前員工說。
在回應Kotaku一系列詳細問題時,育碧表示《怒海戰記》剛剛通過了Alpha階段的測試,並且向我們提供了以下一段簡要聲明。
“《怒海戰記》團隊自上次發表最新進展(譯注:在去年九月)以來做了許多工作,遊戲也在最近通過了Alpha階段的測試,團隊會適時向大家公布更多詳細訊息,我們對此感到十分自豪與激動。但與此同時,我們的遊戲和相關決策正經受一些無中生有的猜測,這些流言只會打擊開發團隊計程車氣,現時他們正全力以赴地開發一款讓玩家感到激動人心、能夠實現玩家們高期望的全新遊戲系列。 在過去的數年裡,為了打造一個安全、更加包容的工作環境,我們在管理原則和開發流程上做出了重大改變,以此保證我們的團隊能更好地製作遊戲,並符合當下世界的多元化趨勢。”
原本的構想很簡單。育碧新加坡工作室負責研發了《刺客教條4:黑旗》中的海上航行玩法,它後來也被證明是這個遊戲最好的部分之一;當時他們還營運著一款名為《幽靈行動:魅影》的免費多人遊戲,並從中獲取了豐富的多人遊戲製作經驗。現在,《黑旗無限》只需要把前面提到的技術和經驗集中到一起,盡最大可能重複利用《黑旗》裡的元素,就可以很快做出一個爆款多人遊戲。不過當時小規模製作的設想很快就趕不上現實情況的發展。
在當時,PS4和Xbox One剛剛發售,而《黑旗》的內核大多繼承自前作日益老舊的技術,在次世代來臨之際顯得愈發過時。
“科技是不斷發展的,要不了多久玩家就想要更好的畫面,到那時開發者才發現舊的技術容納不下新的效果了。” 一名前員工說, “你想改變的東西越多,就會有越多的部分變得過時。假如一個項目被拖延了數年之久,那你最開始的設想也就不再適用了。”
育碧最終決定放棄《黑旗》,轉而開發一個全新的3A遊戲,但它依舊圍繞海戰,也繼承了一些《黑旗》的故事背景和視覺風格。因此,《怒海戰記》應運而生——當時的代號是 “自由計劃” 。不過,真正的麻煩事才剛剛開始。
“紙面上,製作《怒海戰記》沒有什麽難度,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 一名前開發者這麽說道。
據開發者們的說法,他們在開發前階段曾經討論過《怒海戰記》的很多種可能性。有一陣時間,它的背景選定在加勒比海,然而不久之後又搬到了印度洋上。有一版提案的靈感來源於《席德梅爾的海盜》,舞台定在一個名叫許珀耳玻瑞亞(Hyperborea)的傳說國度,遊戲還可以拆成許多個長達數周的多人戰役。還有開發者說,另一些人想建立一個精密的海上基地,一個 “水上大教堂” ,名字叫利伯塔利亞(Libertalia,又譯自由之地),啟發自傳說中的馬達加斯加海盜烏托邦。許多提案還沒個雛形就被廢棄,但因為這個遊戲的核心設定被推翻得比翻書還快,工作室成員們隻得花費許多時間一遍遍重做概念設計。

2017年前後,工作室重整旗鼓,決定回歸海戰要素,因此《怒海戰記》再一次大改,這次是模仿一局定勝負的槍戰射擊遊戲《虹彩六號:圍攻行動行動行動行動》。這個版本就是我們在2017年E3遊戲展上看到的,但在不斷重複的PVP體驗之上,育碧還需要創造一個龐大的世界和任務才能做出他們想要的 “宏偉海盜探索” 遊戲。於是在2018年的E3展會上,《怒海戰記》帶著能夠PVE和自由探索的 “海盜獵場” (Hunting Grounds)模式閃亮登場。這裡和《全境封鎖》的 “暗區” (Dark Zones)類似,玩家可以掠奪據點、彼此戰鬥,或是共同合作擊敗更強大的AI敵人。
但是,這個版本後來也被廢棄。到2019年,生存類型的遊戲比如《荒野求生》和《方舟:生存進化》成了《怒海戰記》的啟明星。除了航海、戰鬥和劫掠,新的版本還加入了資源管理的玩法要素,例如製作和貿易。死亡的代價變高了,因此海盜的傳奇一生還多了一些rougelike要素。總共五名現任和前任員工都表示,這次開發方向的轉變尤為混亂。遊戲採用的引擎難以支撐起在地圖上探索、收集資源的玩法,增加更多物品也讓開發變得更加困難。
到了2020年,四名現任和前任員工向Kotaku證實,開發方向再次改變。最新版的《怒海戰記》還是會不太一樣,不過許多人都不太清楚最終做出來的遊戲會是什麽樣的。與其說這個遊戲離終點線還很遠,倒不如說它連自己的終點線在哪裡都不清楚。
“遊戲內容還在變。” 一名現任員工說。 “人人都知道育碧遊戲應該是什麽樣的,只是遊戲的設計方案依然沒有成型而已。”
問五個參與過《怒海戰記》項目的人問題出在哪裡,他們會給你十個不同的回答。有人責怪遊戲開發缺乏明確的方向,上級領導的決策層層傳遞下來,卻沒人願意擔起責任發號施令執行決策。有人覺得這個項目從最開始就在趕工,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用最簡單方便的那一個,到後來卻不可避免帶來大麻煩。育碧新加坡工作室對製作原創3A遊戲也不熟悉,有些開發者覺得這個工作室還應對不來,其他人則歸咎於創意團隊(位於育碧總部,像 “索倫之眼” 一樣監視著所有工作室的開發),認為是他們對於高層委員會的想法過分言計聽從。在開發遊戲的過程中總會犯錯,但《怒海戰記》的團隊似乎從來沒有做對過任何事。
一些員工發現,團隊內部從一開始就有文化差異。從《刺客教條》製作團隊來的員工習慣決策自上而下傳來,把所有事情劃清職責。而從營運多人遊戲《幽靈行動:魅影》那邊來的員工則更習慣產品的反覆迭代,組織結構也更加平行。
按道理,兩邊團隊的專長應該相互補充。但實際上,有些前員工表示,這種合作只是徒增混亂。
這個項目已經換了第三名創意總監。現任的這位名叫伊麗莎白·佩朗(Elisabeth Pellen),她之前在育碧巴黎的創意部門裡擔任副總裁。前一任創意總監是賈斯汀·法仁(Justin Farren),有人說這是個富有天才想法的人,但對這個遊戲的前景缺乏清晰的認識,無法匹配高層的期待。再前一任是塞巴斯蒂安·普埃爾(Sebastien Puel),他曾經在蒙特利爾長期擔任《刺客教條》的製作人,但據說他對多人遊戲的設計幾乎一竅不通。五名員工說,每次新來一個創意總監,整個團隊領導層都要大換血,從製作人到經理再到各個創意部門的領導,他們全都會離開團隊到國外的另一個工作室去。這樣的大重組幾乎貫穿了《怒海戰記》項目的整個製作周期。
一名前員工說, “每次我們從巴黎那邊收到反饋,他們就會反應過度,把什麽東西都換個遍,再把正在工作的人調走,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幾次了。”
每次新官上任,他們都會在項目管理上按自己的習慣大刀闊斧地改動,但每次都會像之前的團隊一樣重蹈覆轍。像 “玩家到底是扮演海盜還是扮演船” 這種基礎的問題被反反覆複地提出又解決。在2017年和2018年的E3期間,玩家是在扮演船;然而佩朗接手之後,她讓團隊設計上岸徒步探索島嶼的玩法。現有的開發工具和組件是為了水上開船而準備的,陸地移動需要的是另一套東西。根據三名員工的說法,《怒海戰記》光是在這些瑣事上就損失了六個月到一年的開發時間。
而且,哪怕製作進度在推進,玩法設計卻在倒退。
一名前員工說, “他們開始問團隊要2016年的設計案,因為他們又想要做回那種遊戲了。我們兜了一大圈,最後隻加了一大堆製作功能。”

關於任務結構、角色進度,以及究竟是採用無縫開放世界還是小塊區域場景這樣的問題也不斷被提及,看似得以解決,但不久之後又舊事重提。《怒海戰記》要採用像其他育碧遊戲一樣的大地圖開放世界,還是像《戰甲神兵》這樣的遊戲,拆成較小的、相互隔離的區域?前一個領導的團隊決定用一種,換了個新領導之後又變成了另一種。到最後,無論哪種解決路徑,整個團隊都會像之前一樣撞上同樣的問題。
“這就是典型的管理失誤,只不過維持了整整八年。” 一名前員工說, “除了給遊戲加入一些新意之外,我們基本上一直在原地打轉。”
這種混亂的最初階段他們並不是獨一家,但《怒海戰記》團隊裡的混亂局面從未停止過。不僅有反反覆複的項目重啟,整個團隊還要基於這份不斷變更的藍圖開展製作。在2015年,總共有大約一百人在製作《怒海戰記》,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已經接近四百,其中不乏來自其他育碧工作室的開發者,然而他們參與製作的這個遊戲的基礎設計仍然在不斷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並沒有選擇把開發團隊縮小到數十個人,讓這些人 “找到遊戲的樂趣” 並且製訂全新的開發前景;反而,數百個人朝著不明確的目標晝夜不停,絲毫不清楚遊戲的開發方向已經一變再變。
“每次遊戲一變,各種要求、進度、遊戲內經濟和玩家驅動點全都要跟著轉。” 一名前員工說道。 “在一局定勝負的遊戲模式裡,可能你只需要關注彈藥,你的轉向技術,還有玩家等級是多少。但在生存遊戲模式裡,你要在意的就是據點該建多大、一船應該帶多少香蕉、這些貨物該怎麽出售才能最大化收益。”

在為這些問題吵得熱火朝天的同時,團隊成員同樣有事可忙活。有些人樂在其中,每天創作高品質的貼圖和設計,就像他們還在蒙特利爾或者魁北克的工作室、為最新一作《刺客教條》而工作時一樣,可到頭來他們的作品只會被廢棄不用。有些人可不樂意那麽認真,懶得為一個徒勞無功的項目枉費精力。
一些人向Kotaku透露,加班趕工在E3展示或給總部成果驗收時是很尋常的,不過有人表示在育碧新加坡工作室,這根本不算回事,完全沒有其他地方那麽嚴重。相反,他們說,一直做同一件事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卻根本看不見有意義的進展,這才是在這裡工作期間讓他們感到精疲力竭的點。
一名前員工說, “如果沒什麽是定下來的,你的團隊就不會全力以赴。如果你產出的東西幾個月之後就會被丟掉,那麽你產出的品質也是無足輕重的。”
三名現任和前任員工說,這些年來不斷有人從工作室 “逃離” 。
“《怒海戰記》項目團隊裡的人越來越年輕,我之前很少見過。有資歷的、有才華的人會經常選擇離開。” 一名前員工表示。 “人們進來了解了這個項目,看到它的運轉流程和其他各種東西之後,就會選擇離開。這種事情很平常。”
有些人離開是因為這個項目不斷拖延,有些人是被挖走的,他們去了拳頭、騰訊以及臉書之類的科技巨頭在這個地區新開的辦公室。一些員工說,這些崗位不僅薪水豐厚,他們辦公室的秩序至少也在正常運轉。
育碧新加坡工作室在Glassdoor網站上的評價頁面充滿各種抱怨:缺乏競爭力的薪水、工資歧視、辦公室政治,還有自視甚高的惡劣管理層,使得項目難以成功,最終導致雇員外流。這些人同樣也要為《怒海戰記》的難產負責。根據一些消息源稱,有些高層經理會在身邊安插一幫 “馬屁精” ,拒絕接受任何來自工作室成員的意見或建議,而且還會向巴黎總部的人誇大遊戲的開發進度,而當下的資源和時間安排完全沒法達到這些人所說的目標。如果有人對現狀持續表示不滿,他們可能會 “消失” ,要麽去了另一個團隊、另一個項目,或者是另一個工作室。
“這種彌漫在新加坡工作室的惡性辦公室文化同樣要負很大的責任。《怒海戰記》的種種問題——重啟、重塑、從頭再來——這些荼毒了遊戲開發將近十年的問題,和它逃不了乾系。” 一名前員工說。
或者按照另一位開發者說的那樣, “從一開始,這個項目就是被恐懼推著走的。”
辦公室裡的一些問題在去年育碧深陷性騷擾、職場霸淩等醜聞的同時一同爆出。不過,那三個消息源稱,除了把那幾顆老鼠屎挑出來之外,新加坡工作室依然迫切需要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
《怒海戰記》並非唯一一個在2017年E3遊戲展上曇花一現的育碧遊戲。雄心壯誌的開放世界太空歌劇《神鬼冒險2》也在其列,同屬其中的還有Massive工作室的《阿凡達》遊戲改編。在這幾個遊戲現身的那段時間,法國媒體業巨頭維旺迪正計劃對育碧展開惡意收購,威脅要摧毀這家有幾十年遊戲製作歷史的家族企業。兩名前員工告訴Kotaku,這起惡意收購也部分導致育碧如此著急要在開發早期就把這些遊戲公布出來。
《阿凡達》的遊戲重新浮出水面,命名為《阿凡達:潘朵拉邊境》,並公布了2022年這個大致的發售時間。至於《神鬼冒險2》,它的開發困境在去年已經被一家法國報紙"Libération"全面報導過。初次公開四年之後,它依然沒有確定發售日,在上個月的E3遊戲展中,育碧對它也隻字不提。育碧似乎認識到,老一套的大製作遊戲開始行不通了。

在五月的財報會議上,育碧表示將轉移其戰略重心,減少對大製作遊戲的依賴。儘管育碧仍然有諸如《刺客教條:維京紀元》和《極地戰嚎6》這樣的3A大作,它的收益更多來自其他地方,包括免費遊戲。不過,育碧對自家王牌IP的策略同樣在發生改變。這個月早些時候,育碧公布了《刺客教條:無限》,它會像《要塞英雄》和《GTAOL》一樣是一款不斷更新的遊戲。據彭博社報導,這將會導致《刺客教條》開發團隊內部結構的巨大變動。
然而相比之下,《怒海戰記》的開發前景似乎便不甚清晰。紙面上,《怒海戰記》的早期構思與《刺客教條:無限》公布的消息非常相似,而且《盜賊之海》的成功也印證了海盜模擬遊戲的可行性。許多《怒海戰記》的開發者對遊戲最終發售、是好是壞已經不抱希望,他們隻想盡快從這個項目中解脫。不過其他人知道,在現在這個 “遊戲即服務” 的天下,遊戲的發售日並不是遊戲製作的結束,這還僅僅是個開始。
“我熱愛電子遊戲,因為真正的創新和魅力來自我們的開發團隊和玩家們創作的自由。” 伊夫·吉勒莫特(Yves Guillemot),育碧的聯合創始人兼CEO在維旺迪惡意收購的舉動達到高峰時說了這麽一番話。 “創新的自由,自我表達的自由,承擔風險與享受樂趣的自由。”
“如果你是自由的,你的人生中就沒有失敗” ,他說, “所做的一切都是前進。” 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對於《怒海戰記》而言這句話究竟是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