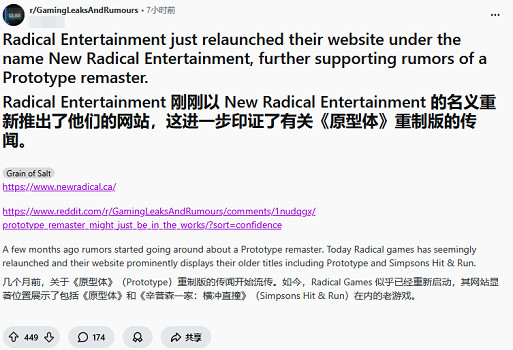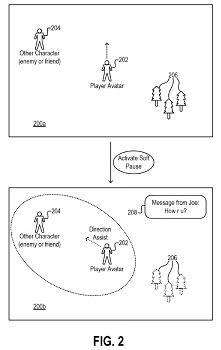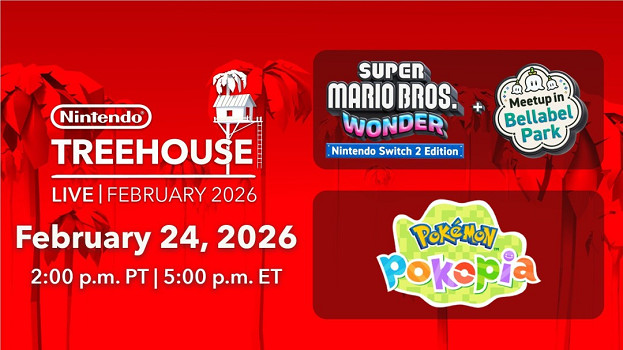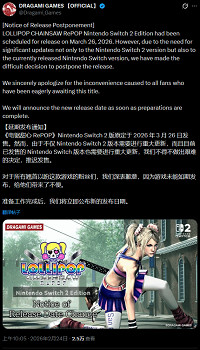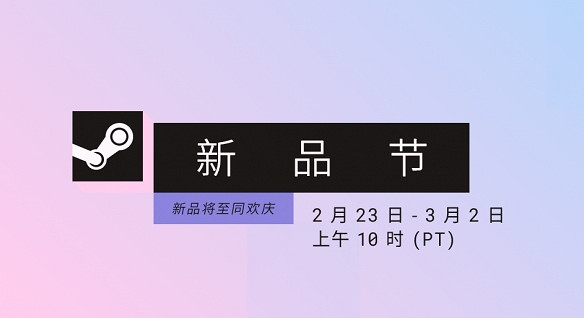摘要:這次,你不再是監視者了。

【1】
“終於全都得救了。”
在通關Warm Lamp(暖燈)工作室的新作《Beholder 2》後,我坐在椅子前長舒了一口氣。
由於這次有國內的東品遊戲參與發行,《Beholder 2》的文本翻譯比前作好了很多,至少沒之前那麽重的機翻痕跡了。而遊玩過程中最明顯的感覺,是主角不像前作遊戲中那麽“無能”了。
《Beholder》的初代兩年前火過一陣,那時玩家需要扮演一個極權國家的樓管,監視租戶、偷聽對話,然後舉報“思想不夠純潔”的鄰居。
但由於主角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公務員,自己家也有本難念的經,有著生病的女兒、缺錢讀書的兒子,玩家需要在良心和利益之間來回掙紮,決定靠不靠“惡意舉報”謀取私利。
這也讓遊戲裡的所有角色很難都有Good Ending:
狠得下心做壞人的,成了忠犬,按要求兢兢業業地處理了所有住戶,性命無憂卻得不到良心安寧;
做善人的,幫助無辜房客偷渡海外、把兒子送出國避難,自己卻在半夜被拖進警車殺頭。

就算通過無數次試探後總結出了“完美”路線,避開了秩序部的監視,讓自己和家人成功逃到海外,也不過是一家人得救,幫助過你的人們仍然在水深火熱之中。

初代很多差評都來自“無能為力”
因為Warm Lamp是一家俄羅斯工作室,所以當年很多玩家都評價說,這種哪條路都是苦路的感覺,有種俄羅斯歷史的既視感。
《Beholder》這個名字,也成為了對遊戲最好闡釋——你的工作是一名監視者。而就算你再努力,在漫無邊際的黑暗中苦苦掙紮,到最後也隻不過是一個監視者。
【2】
玩家們可能已經厭倦了做“怎麽選都不爽”的道德抉擇。
近幾年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抉擇,可能是《巫師3》的血腥男爵任務線。不論傑洛特在遊戲中選擇如何與多方勢力博弈,最後都沒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當年玩到這裡,不論男爵本身多麽人渣,玩家們都多多少少產生了一絲共情。
但到了去年的《冰封龐克》,就因為結局畫面加了一句“但這一切值得嗎”,就遭到了玩家的大規模非議:我玩個遊戲,費盡心機抓生產、救世界,結果人都快餓死了還要執著加不加班,矯不矯情?

《冰封龐克》的道德拷問
為什麽有的道德抉擇打動人心,有的道德抉擇卻讓人心生膈應,這其實是一個主菜和配菜的問題。
道德抉擇讓不讓人厭煩,除了它本身的劇情設定是否合理之外,還在於它是敘事的目的還是手段。
在反烏托邦遊戲裡,“為抉擇而抉擇”曾經是一種慣用手法。或者說,這個題材之所以成為大量獨立遊戲的創意源頭,在於它有一套非常易於執行的“劇情——玩法——拷問”三層結構:
從最早的《請出示檔案》(Paper, Please),到《奧威爾》(Orwell)系列和《頭條新聞》(Headliner),都逃不開這個結構:
劇情,可以直接取用反烏托邦作品完善的世界觀:
大多數的反烏托邦遊戲,藍本都無法脫離經典的反烏托邦三部曲:紮米亞金的《我們》、奧威爾《1984》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其中又以《1984》為甚。
常見的框架大家也很熟悉,有一個精神狀況壓抑、充滿個人崇拜、極端國家主義的社會,而我們的主人公卻在其中覺醒了自由的思想……在這樣的世界觀裡,衝突是天然存在的,擁有著自由思想的個人(玩家)必然反對威權,鬥爭——反抗的橋段非常自然。
玩法,在劇情的對立框架下可以設計得成本十分低廉:
有了大社會和小人物的對立,遊戲的玩法可以全部聚焦在“扮演一顆螺絲釘”上,把在極權社會的日常工作遊戲化,就有了《請出示檔案》裡面成天檢查檔案的公務員,《奧威爾》裡鑽研個人資料、琢磨抓捕“罪犯”的調查員。

很多“反烏”遊戲的玩法互動都是和檔案打交道
而最後打動玩家的關鍵點,就在於陷入兩難境地的道德拷問:
作為一個與社會主旋律相悖的異類,玩家要麽選擇同流合汙、要麽選擇反抗救世,前者讓你良心不安,後者讓你遇到現實難題。
這三層結構之所以成立,全都基於反烏托邦題材的基礎世界圖景:你是一個生活在下行的世界中、難以為自身做選擇的弱小個體。
所以很少有製作組會一直把這個題材拿來用——反烏托邦遊戲的情感內核實際上同質化比較嚴重,看多了也就膩了。
對於玩家來說,對反烏托邦的情感想像也十分容易消耗。
明朝文學家徐渭論詩時說過,“好詩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這種“陡然一驚”的打動,就是反烏托邦題材觸及人性時的感覺。
但遊戲是遊戲,天天用冷水澆背是行不通的。
【3】
所以在《Beholder 2》裡,Warm Lamp做出了他們的變革:
讓反烏托邦遊戲脫離敘事小品的框架。
反烏托邦可以是奧威爾式的,也可以比奧威爾的故事走得更遠——我們的主角不僅僅只能是《1984》裡的溫斯頓,更可以是《V字仇殺隊》的“V”或是歷史上的羅伯斯庇爾。
《Beholder 2》延續了前作的世界觀,Warm Lamp決定把前作一個模糊的極權國家勾勒得更為完整,世界也從遠東的角落來到了國家的權力核心地帶:“真理部”的大廈之中。

而你的主角,也不再是前作中孑然一身的樓管,而是落馬高官的後代,目的是憑借自身能力在權力的的階梯中爬到高處。也正是如此,玩家終於有機會能夠動用自己的權力直接改變這個糟糕的社會。
遊戲的視角也完成了一次維度轉換:從前作封閉在一棟公寓中的單屏模擬經營遊戲,變成了一個有立體場景的多元世界。

《Beholder 2》沒有了前作中緊緊壓迫的時間線,有了更濃鬱的RPG感:
你的每一天都是自由的,可以選擇推進主線劇情,也可以花費時間工作賺取金錢和聲望,或是通過看書、看電視劇來把自己的角色培養出更多樣化的能力。
“像螺絲釘一樣工作”也顯得沒那麽必要:比起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的同事們,每分析完五張表格才能獲得可憐的100聲望和一點金錢,你只要學會投其所好,在工作時間幫老闆“解決一下生理問題”就能獲得過萬聲望。

工作得來的報酬還都被拿來做這種事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通過辦公室政治的手段,把你的同僚全部搞倒。所有跟我競爭的人都被被趕跑了,自然就只有我晉升了。而最簡單的小手段(就像在前作裡搞房客一樣)就是在他們的工位上放上各種違禁品,然後舉報之。

他人也在不斷“忠告”你做壞事
在獲得了足夠多的聲望晉升後,你的工作內容也有所改變。隨著層級升得越來越高,工作內容便開始展現出整個“真理部”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方式——但在這裡,我們就不多劇透了。
這也是《Beholder 2》相對前作最大的創新:雖然仍然是半線性遊戲,但為了達成晉升的目的,玩家可以選擇走上不同的路線,而這些路線都是可行的:
你完全可以做一個不損人利己,堅守了自己正義自由的內心的人,為了晉升老老實實工作:
填表,蓋章;填表,蓋章;就像《請出示檔案》的主角一樣,在荒謬的機械性工作裡完成自己作為工具人的使命。假以時日,你就能慢慢登上高位,但這可能要花上幾十年時間。

核心是工作,卻不是必須得工作
或者,你可以使用那些放在那給你用的伎倆,但這次的不同在於,哪怕你選擇“與人鬥”,也可以有更多不傷人性命的方式。
比如有個人慫膽小的同事A,為了扳倒他你可以選擇和同事們一起捉弄他、讓他崩潰;也可以選擇和他成為朋友,撮合他和女同事(然後讓他們一起滾蛋)。每一種不同的選擇,都導向不同的結局。
那些在過去作為敘事目的的道德選擇,在本作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你不會遇到不去做壞事,故事就完全沒有辦法繼續的困境。
它們只是不斷提醒著你,晉升之路越快,路上他人的鮮血就越多。
【4】
Warm Lamp沒有直接選擇讓道德困境侵入玩家,而是留給了玩家足夠的操作空間。
作為高官的後代,在晉升的主線之外,玩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收集父親留給你的生物指紋箱,這涉及到最終結局的選項多寡。
只要你在主要遊戲中爭取的足夠多,在攀升到高位之後可以選擇貫徹自己的自由意誌,締造自己想要的世界。

不過,玩家最難達成的結局,既不是摧毀體製,解放一切;也不是爬到最高位,成為獨裁者。
在這裡,Warm Lamp沒把最終的道德議題明白地寫在紙上,而是把這個問題留給了玩家思考。
你可以到達高位後用政治手段除盡那些極權官員,但這也提醒著你:通往善的手段可以是非善的嗎?
你可以通過強力的技術手段強制保證民眾的自由,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服從於什麽,假設是服從於我們的自由意誌,那如果自由意誌是系統創造出來的假象呢?
這是Warm Lamp對反烏托邦遊戲議題的升華:我不必再灌輸給你《1984》的故事——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了,你要做的,是在《Beholder 2》中爬上高位後,寫出自己的答案。
根據我們從《Beholder 2》國內代理商東品遊戲那裡了解到的消息,Warm Lamp也給《Beholder 2》開發了移動版,近期就會發售。如果你還沒有來得及在Steam上體驗它,也不妨在手機上感受黑暗款的“杜拉拉升職記”。